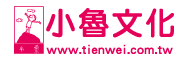先父陳立峰君,字小魯,故常以「小魯」、「胡魯」為撰稿的筆名。記得幼時懵懂好奇,不明白「魯」為何意,便問父親,父親就告訴我說,立峰是站在山頂的意思,因孟子盡心篇有云:「孔子登東山而小魯,登泰山而小天下」,他自己年少輕狂便以「小天」為號。爾後閱歷漸增,不免覺得狂妄而汗顏,所以退而以「小魯」自勉。況且孔子以「魯」興志,魯國雖小,卻可為天下之化首。
我雖愚鈍,不明究理,但父子之間簡短的對話,仍讓我印象深刻。
父親熱愛工作,早起探黑,筆耕不輟,每日上午,常見三、四位報社、電台、期刊或印刷厰取稿人員坐等家中,無論是社論、專欄、評述等文稿,只見他洋洋灑灑,一揮而就。最多至11點左右,都能一一完成,陸續交件。不喜作文的我,看在眼裡總不免納悶不解。父親的忙碌,讓家人無法常常與他有談話的機會。母親知道孩子的期待,便常對我和姊姊說,你們的爸爸是屬於國家天下的,別去煩他。語氣中有些許無奈、嘲諷,但多的是傲然與自立。
父親曾任職過數家報社,亦曾兼辦過多種雜誌刊物,其中印象最深的就屬文星雜誌了。記得小學期間,自蕭孟能先生(文星投資者)初次來家裡談話後,便不時來討論創刊事宜,每至深夜凌晨1、2時欲罷不能。後來從母親口中知道,父親是與夏承楹(何凡)、林海音夫婦應蕭先生之力邀,籌辦此刊物。夏先生與父親為當年北平華北日報同事,交誼甚篤。而蕭先生的尊翁蕭同兹先生本與父親爲新聞界舊識,故孟能先生緣此而結交。
從那時起,家中更是文化界諸先輩經年累月出入之所,老中青三代常共聚一堂,高談濶論,縱橫古今;月旦人物,臧否時事。彼時讀小學的我,儘管得天獨厚,家中坐擁數十種報章雜誌,每曰貪婪瀏覽無法自拔,但對長輩們的對話內容,常常無以串接,而只是片段、零星的半知半解。所幸經由奉茶倒水、隔牆側耳傾聽這樣精采的話語,畢竟彌補了些平日無暇於父子交流的疏離。
印象所及,「文星」自創刊開始,由於文星書店辦公空間及往返耗時等諸多不便,因而所有的編務全都在父親的大書桌上進行著,夏伯伯與伯母則經常至家中討論出刊事宜,我和姊姊最喜歡聽的就是他們兩位那口京片子的腔調,抑揚頓挫,明朗暢快。可惜的是,這情景維持了一段時間後,他們便逐漸淡出此刊物。爾後數年至父親辭去主編之職為止,一直都由其獨自承擔所有編務,除策劃選題、封面人物會與各專業領域的朋友諮商外,其餘約稿、照片、版面、印務、校對,甚至推廣等工作全部一手包辦。耳濡目染下,這對我長大後經營出版編務,確有一定的影響。其中至今最感自嘆弗如的就是他的筆勤與耐煩,海內外大量投稿者幾乎無日無之,父親皆盡可能地回函建議、討論、感謝或鼓舞後進,哪怕片紙隻字的便條式回應也不願漏掉。遙想當年,我在覬覦蒐集各方來函郵件上五花八門的郵票之餘,多少也領悟到一些人情世故吧!
有關「文星」這些編務林林總總,在父親過世時的文星第65期中何凡先生的紀念文裡亦有所提及。夏先生與海音女士是君子人也,他們的恩怨分明與不掠美,一直是我心目中尊敬與想念的前輩。在我冷眼旁觀了近五十年的歲月裡,台灣在經歷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各方面的巨大變遷下,如果「文星」有過一定的影響力,那也難怪總會有人以它和自身的關聯為榮,有時刻意的提及或刻意的不提及只會令人啞然。
其實社會的進步必定是眾人努力的結果;一份有力量的刊物,也是眾志成城的產物,尤其是默默付出,不為名利的中堅分子。那些在我家客廳中經常出現的知識分子們,如成舎我、葉明勳、毛子水、鄭學稼、胡秋原、方豪、馮志翔、殷海光、林金開、張繼高、胡汝森、徐復觀、居浩然、王洪鈞、夏曉華、李靈君、張隆延、朱介凡、黃華成等諸叔伯先輩,以及像李敖、陳鼓應、鮑奕明、陳麗生等較為年輕一代的俊彥,彼等或力陳己見,或沈吟思索,或面紅耳赤,在政治、輿論的低氣壓下,每欲破繭而出,亟思改變。當年作為少數能夠探討國家社會文化何去何從的討論平台,文星很快成為耀眼的明星;同時也成了權力當局眼中的焦點。猶記不下二、三回於晚餐的餐桌上,父親曾臉色凝重的對母親說:得罪當局是必然的,只是儘可能地取得釋放與平衡。如果有一天我出門未再返家,妳就帶孩子自求生路吧!當然,我們不會革誰的命,所需要做的只是耕耘與等待公民的成熟;因為一切情緒性、過份觸怒當道的言論,只會中斷這樣的努力成果。
對於雷震先生與「自由中國」的遭遇,他一直認為知識份子應該得找出另一條改變社會的道路,因此「文星」在創刊時的封面及發刊辭中即表明了它的定位:是生活的、文學的、藝術的,爾後則調整為思想的、生活的、藝術的。意即不必直接衝撞政治的敏感神經,應該自下往上,以更為開濶、相對迂緩而有力度的姿態,浸潤灌溉這個一向由上而下、飽受壓抑、閉鎖、焦躁的社會。一旦具素養的文化識見匯為洪流,政局自然改觀。父親因此對待那些才華洋溢、不滿現狀的青年俊彥特別心疼與呵護,亦曾多次提及國家未來的精英,切莫斷送在齷齪的政客之手,吾輩當以大德敦化為念,莫以小德川流為喜。否則此一難得建構的媒體,極易遭到停刊。一本雜誌的存續原非什麼大事,不過在台灣當時的文化、政治悶局下,這株奮力崛起的幼苗,是需要相忍為謀,躁進反易斷送或遲滯應有的發展。
但即便如此,仍有心切者不以為然,認為邊緣策略猶嫌不足,時以鼓動風潮、立轉乾坤為尚。在那個商業、廣告沒有發展的年代,唯賴銷售量的市場算計或許也在其中,畢竟苦撐之局對理想主義的堅持與不變質,永遠是嚴峻的考驗。記憶所及,海音伯母便曾在客廳中,力勸父親不要再繼續擔綱,否則吃力之餘,絕對裡外皆討不了好。
言猶在耳,「中西文化論戰」方酐,原本為文化前景論證的美意,逐漸夾雜太多意氣言語。其中在父親過世前頗為鬰悶、遺憾的一件事還是發生了,那就是與胡秋原先生的對簿公堂。「文星」社長(蕭孟能)、主編(父)、作者(李敖)同為胡先生的被告;胡原為父親老友,李則為父親向來惜才的青年,即便出言辛辣鋒利,亦屬氣盛使然;且胡先生之為文亦不遑多讓,何苦以司法訴訟來定文化思想上的是非。此外對於李先生的文章,主編本有把關修刪之責,不足為怪;唯對於孟能先生竟在父親已將關鍵字句刪除並已付梓後,卻私下至印廠補回一事,頗覺懊惱,但在開庭時卻因多方顧慮而不願說明真相。一來實不忍李先生剛剛展露頭角之際便遭挫折;二來與蕭先生之父又為故舊之情,因此僅能以私人立場懇勸胡秋原先生諒解多方,自身辭去多年耕耘奠基的「文星」主編,希望事緩則圓。惜官司未了,人卻因心臟病突發而離世,時年不過四十五歲,「文星」自此與他恩怨俱了。當時的我,年僅十三歲,家無恆產,父親只留下一屋子老舊的書報雜誌。慶幸的是,這樣的遺產讓我在長大後反而成為出版資糧。
後來自母親口中得知,當初父親最耽心的就是,表面單純的訟案,如果恨意太深必然會讓政治力有機會介入。這對缺乏背景人脈的一方甚為不利,甚至好不容易播下的種子,亦可能遭到剷除,這對台灣整體文化的發展是極為不值的事。
令人遺憾的是,「文星」後來果然還是遭到停刊的命運。或許,它已完成了階段性任務;或許,多元、深邃、理性的對話場域永嫌不足,因為文明通常來得很慢,一不留神,粗鄙野蠻就迅速重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