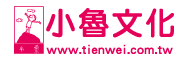奧斯德里茲火車站,是我星期二和星期五放學早的時候,經常出沒的地方。
我喜歡來這裡看火車出發時,人們臉上流露出的種種情感。觀察人在各種情境下自然流露的感情是我的一大愛好。比如,足球比賽的時候,球員在進球以後互相擁抱,邊跑邊用手在空中做出各種手勢,一個接著一個把自己像沙袋一樣往草坪上摔出去。再比如,「誰將贏得一百萬」裡面那些女性參賽者,每次只要答對了問題,她們總是會把手放在嘴巴上做出驚喜狀,然後把頭往後面仰,開心地大叫起來,還淚眼汪汪的。
火車站裡人們的情感則通過眼神和手勢傳達著。有即將離別的情人,有結束假期準備回家的老奶奶,有衣著光鮮在男人陪伴下的女士。我觀察著這些即將離開的人們,不知道他們要上哪裡去,也不知道為了什麼要離開,更不知道會離開多久。他們或者隔著火車的玻璃窗戶互道再見,或者做個離別的手勢,也有人徒勞地大喊著,哪怕對方早已經聽不見。有的時候,這些送別的人流露出的感情如此強烈,讓你覺得周圍的空氣都因為他們而變得濃稠。這些人沉醉在離別的萬千情緒中,世界對他們來說好像是不存在的。火車到站時也是同樣的場面。我站在月臺的最前面,觀察著來接旅客的人。他們的臉上寫著焦急和緊張,雙眼尋找著,然後突然嘴角邊漾起一個笑容,他們揚起手臂激動地揮舞著,接著往某個方向走去,和他們等待的人擁抱在一起。是的,我喜歡這些人們任憑自己的感情傾泄流淌的場面。
這就是為什麼我今天又出現在奧斯德里茲火車站的原因。下午四點四十四分有一列從克萊蒙費朗開來的列車,這班車是我的最愛。搭乘這班車的人什麼樣子都有,年輕的、老的、衣著體面的、胖的、瘦的,上半身穿的和下半身完全不搭調的。我如此專心地注視著這些從車上走下來的人,以至於完全沒有注意到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。通常我專心做某樣事情的時候,就算有頭長毛象踩了我的腳,我都感覺不到。我轉過身去。
「你有沒有香菸?」
她穿著一條很髒的卡其褲,舊罩衫的袖子一直捲到手臂上,脖子上圍著一條只有在我奶奶的衣櫥裡才能找到的舊圍巾。
「我沒有香菸,對不起,我不抽菸。 如果你想要的話,我有薄荷口味的口香糖。」
她不滿意地撇了一下嘴,向我伸出了手。我把一整包口香糖都給了她,她往包包裡一塞。
「你好,我叫諾,你叫什麼?」
「諾?」
「嗯。」
「我,我是……盧‧貝爾蒂尼亞克。」
每次我跟別人說我的名字叫貝爾蒂尼亞克,人家都以為我跟歌手路易‧貝爾蒂尼亞克有什麼血緣關係,還有的人以為我是他女兒。國中的時候,有一次我騙同學說,我就是貝爾蒂尼亞克的女兒,結果他們不但相信了我,還要我幫他們簽名。
可是今天當我說出自己的名字時,對方卻完全無動於衷。我跟自己說,也許她不喜歡聽這一類的音樂。她向離我們站的地方幾公尺遠的一個站著看報紙的男人走去。男人抬眼看看她,嘆了口氣,從口袋裡的香菸盒抽出一支菸。她一把拿過香菸,看也不看那個男人,又朝我走回來。
「我在這兒見過你,好幾次了,你來這裡幹什麼?」
「我來這裡看人。」
「你們家那裡沒人可看?」
「有是有,但是和這裡的不一樣。」
「你幾歲?」
「十三。」
「你有沒有零錢?我從昨天晚上到現在沒吃過東西。」
我翻了翻牛仔褲的口袋,拿出了身上所有剩下的硬幣,看也沒看就全部給了她。她數了一下總共有多少,然後收了起來。
「你上幾年級?」
「高二。」
「十三歲就上高二?」
「嗯,我提前了兩年。」
「什麼意思?」
「我跳級的。」
「這個我明白,但是你為什麼跳級?」
我心想,她是不是在嘲笑我。但是她看上去一副嚴肅的神情。
「我也不知道。我上幼稚園的時候就已經會認字了,然後到小學二年級的時候跳了一級。
那時候老師上課講的那些東西我已經全會了,於是課堂上我無事可做,只好用手指捲頭髮,然後不停地拉頭髮,結果幾個星期下來,頭皮上被我拉出了一個洞。等到我頭皮上出現第三個洞的時候,他們就讓我跳級了。」
我其實也很想問她問題,但是我不敢。她一邊抽著菸,一邊把我從上到下,再從下到上看個透。她的眼睛好像是在搜尋著,看我身上有什麼東西能給她。
「那你的頭皮,現在好點沒有?」
「嗯,還不錯。」
她笑了起來。她咧開嘴的那一刻,我看見她少了一顆牙齒,是一顆小臼齒。
從小到大,不管我身處何方,我總是覺得自己不屬於這個地方。我總是游離在畫面之外,隔絕在談話之外。好像只有我,永遠能聽到其他人聽不到的聲音和話語。也只有我,別人都聽見了的,我卻充耳未聞。如果世界是個方塊的話,那我就一直在這個方塊的外面,被一扇玻璃門遠遠地隔離在這個方塊的另一端。
然而,昨天我和她一起度過的那段時間,我卻站在圓圈的裡面。那個瞬間,有一個圓圈包裹著我們,保護著我們。
我不能逗留太久,爸爸在等我。我不知道該怎麼跟她告別,是應該稱她為小姐還是女士,或者是叫她諾。於是,我匆匆忙忙地跟她說了聲再見,反正我想她也不是那種注重所謂社交禮節的人。在走出火車站前,我轉過身向她做了個告別的手勢。她站在原地,看著我離開。她空洞的眼神令我明白,她站在那裡,無人可等,沒有家,沒有電腦,無處可去。
這天晚上吃飯的時候,我問媽媽,那些年輕的女孩怎麼會流落街頭。媽媽輕輕地嘆了口氣回答我說,生活就是這樣,充滿了不公平。我常常覺得,人在回答這一類的問題時,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兜圈子。但是這天媽媽的回答卻讓我很滿意。
我的眼前浮現著她蒼白的臉,她那雙因為消瘦而顯得格外大的眼睛,她頭髮的顏色,她粉紅色的圍巾,和她層層疊疊的外套下隱藏的祕密。一個藏在她心裡的祕密,她從來沒有向任何人訴說過。我想站在她的身邊,和她在一起。我躺在床上,後悔沒有問她的年齡。她看上去那麼年輕。
同時,她看起來像是真正了解生活的人。或者說,她了解生活中那些令人害怕的東西。
 炎炎夏日,每天起床後第一個掙扎就是「今天要騎腳踏車還是機車去上班呢?」沒錯,小編現在正在努力瘦身,有時候會騎著腳踏車,搖啊晃啊花個40分鐘到辦公室,晚上再騎回家,藉此平衡辦公室坐整天而停滯消耗的熱量,以及日漸壯大的大腿。可是最近太陽好大,往往剛騎出門就汗流浹背的,實在很傷腦筋,所以會想偷懶,坐上機車發動引擎,一路吹風很涼快啊。但是想到可憐的北極熊還有我粗壯的大腿,不行!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!(是在對誰精神喊話啊?)
炎炎夏日,每天起床後第一個掙扎就是「今天要騎腳踏車還是機車去上班呢?」沒錯,小編現在正在努力瘦身,有時候會騎著腳踏車,搖啊晃啊花個40分鐘到辦公室,晚上再騎回家,藉此平衡辦公室坐整天而停滯消耗的熱量,以及日漸壯大的大腿。可是最近太陽好大,往往剛騎出門就汗流浹背的,實在很傷腦筋,所以會想偷懶,坐上機車發動引擎,一路吹風很涼快啊。但是想到可憐的北極熊還有我粗壯的大腿,不行!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!(是在對誰精神喊話啊?)